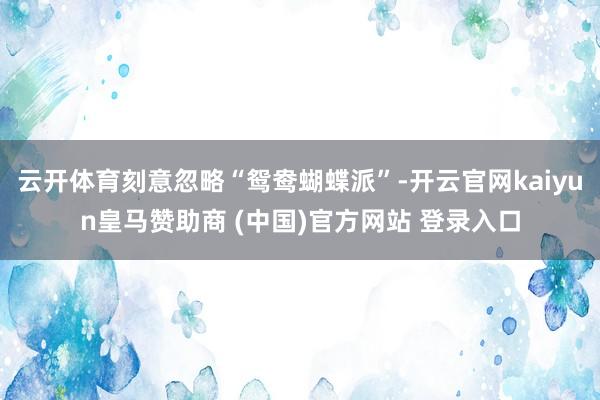

◎唐山
“虽力愿提议月旦主义,而不肯为主义之随从;并不肯国东谈主齐奉泰西之月旦主义为天经地义。”“中国旧有体裁不仅在畴前时间有越过之地位汉典,即关于异日亦有几分之孝敬,此则同东谈主所敢信赖者,故甚愿发表治旧体裁者考虑所得之见,俾得与国东谈主相商量。”在1927年出书的《中国演义史》中,范烟桥这么写谈。
民国时中国演义史考虑之风颇盛,自1920年张静庐的《中国演义史大纲》后,至少出书过40种专著(含翻译),鲁迅、陈景新、沈从文、阿英、胡怀琛等都写过中国演义史。鲁迅的《中国演义史略》自1925年出书后,一度掀翻“演义史热”,范烟桥的《中国演义史》亦被视为“跟风之作”。关于这些书,鲁迅在《两地书》中曾斥“凌乱失实”甚多。
其实,范烟桥从1925年冬便运转写《中国演义史》,历时近两年。体例甚澄澈,将中国演义史分为“演义搀杂时辰”“演义独赶快期”“演义演进时辰”“演义全盛时辰”,仅“演义演进时辰”便列举了27类演义,虽将戏曲与弹词也列为演义,似有欠妥,但包罗万象,稳妥教诲。基骨子现了“以时间为纲,以著述为目,而以作者经纬之。其间条缕,详于目录,既便雠校,又眉清目秀”的创作意见。
学者苏衍丽在《二十世纪中国演义史的编撰与考虑》中以为:“这种体例在一定过程上比鲁著愈加接近当代演义史的编撰边幅了,已是比拟纯属的章节体。”
因《中国演义史》,范烟桥从中学陶冶成了大学陶冶,先后在捏志大学、东吴大学主讲演义课。可见该书确有一订价值。
但是,后东谈主少许说起此书,因范烟桥是“鸳鸯蝴蝶派”的代表作者之一(列入十八罗汉),前引中的“同东谈主”,即指旧派演义家,他们以为胡适、鲁迅等用番邦考虑法写中国演义史态度不客不雅和善,刻意忽略“鸳鸯蝴蝶派”,是以范烟桥要为本派“伸张正义”(据张军《论早期中国新体裁史写稿的四种旅途》)。
在《中国演义史》中,范烟桥对“徐枕亚的《玉梨魂》《雪鸿泪史》、吴双热的《孽冤镜》、李定夷的《霣玉怨》、姚鹓雏的《燕蹴筝弦录》、李涵秋的《广陵潮》、张春帆的《九尾龟》等进行了与胡适、鲁迅等东谈主不雅点不同的精到点评”,笃定了“平凡体裁家包天笑、周瘦鹃翻译域外演义的历史道理道理”,对鲁迅、郭沫若等虽列作品,不予批驳。
赫然,范烟桥试图将“鸳鸯蝴蝶派”立为中国传统演义正脉,将体裁考虑会、创造社、变调体裁等一概称为舶来。虽提情怀之争,却有两点孝敬:一是厘白皙话演义起源,竖立其原土发展头绪;二是保留大批“平凡体裁”史料,对后东谈主坑害“严肃体裁”与“平凡体裁”的意志界限,重念念传统与当代的筹谋,有一订价值。
《中国演义史》存有偏见,但范烟桥试图从传统麇集当代的舒服视角是贵重的,且书中较充分地呈现了范烟桥的旧学功底与才华。
范烟桥出自书香门户,父范葵枕曾中举,母严云珍是“一个通文墨的女子,尤好弹词”,夫东谈主是吴江名绅沈临庄之女。范烟桥拜国粹人人金松岑为师,金讲课“常须背诵,不可不勤读,常常至夜深”,范烟桥动笔快,被金松岑称为“扬帆沉,速不求工”。
21岁时,范烟桥向清末民初的上海三大报之一《时报》投稿,被主编包天笑慧眼识中,而后范烟桥的漫笔、演义、评弹等屡见各报,“逐日数以千字,一年之间,合杂著计之,当朝上百万余言”。
范烟桥不写言请,只写诽文,即“告密寰球社会射影含沙之事,为鬼为蜮之形”,他依然电影剧作者和词作者,他为周璇写的《西厢记》插曲《拷红》,被郑逸梅赞为“奥秘应用丧祭句,协平仄韵,吐故纳新,入耳宛转,经周璇运腔使用,遏云绕梁地演唱,不知眩惑了些许影迷”。
抗战本事,范烟桥拒与日伪合营,“咬紧了牙关,束紧了裤带,作念一个苏州东谈主所说的戆大,北平东谈主说的白痴”。
1967年,74岁的范烟桥病逝。他一世著述极多,却因“鸳鸯蝴蝶派”的标签,被当成“平凡体裁”而忽略,从他留住的这本学术性著述中,可知“鸳鸯蝴蝶派”亦有复杂的一面,包含着不同主义的勤苦与坚捏云开体育,亦可成为文化成就的好材料。